
摘要:上海时期鲁迅对苏联电影怀有特殊情感,尤其偏爱革命战争、社会建设、探险纪录等题材类型。作为一种视觉艺术形式,鲁迅认为苏联电影不仅能够透视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建设的真实状况,而且对中国左翼电影发展具有借鉴作用。但是,鲁迅毕竟没有实地考察过苏联,仅仅凭借着苏联电影勾勒的部分图景来想象苏联,中间肯定存在着误读成分,鲁迅的“洞见”和“不见”在苏联观上得到有效体现。
一、上海时期鲁迅观看苏联电影类型概览
1927年10月3日,鲁迅携许广平到达上海,正式开启了在“魔幻之都”的都市生活方式。在平时从事创作和翻译之余,鲁迅的日常娱乐活动便是观影。电影艺术不仅能够缓解精神压力,开阔文化视野,弥补生活经验之不足,而且也是鲁迅积极融入上海都市生活的直接表征。根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在上海时期合计观影140余部,主要以美国、苏联、法国、德国等外国电影为主。实际上,鲁迅除了青睐美国好莱坞影片之外,还对苏联影片怀有特殊情感。据青年学者刘素在《鲁迅与在沪放映的早期苏联电影》的统计显示[1],1933年2月16日至1937年7月15日,上海各大影院相继放映苏联影片26部,其中,1933年2月16日至1936年10月12日鲁迅在上海寓居期间放映13部,除了无缘观看《重逢》《金山》《无国游民》《怒海》之外,其他9部都在鲁迅观影范围之内。这里,刘素在图表中明显遗漏苏联电影《抵抗》,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因此,鲁迅在上海时期共观看10部苏联电影,时间主要分布在1933年至1936年间,分别是《生路》《亚洲风云》《雪耻》《傀儡》《抵抗》《黄金湖》《夏伯阳》《铁马》《冰天雪地》《复仇艳遇》,其可以划分为三种不同类型。
(一)革命战争题材
此类电影主要描述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国内革命战争的曲折进程,真实地反映俄苏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合法性,尤以《亚洲风云》《夏伯阳》《抵抗》《复仇艳遇》为代表。1917年,俄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这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933年4月7日,《鲁迅日记》记载:“三弟来,饭后并同广平往明珠大戏院观《亚洲风云》影片。”[2]371此片又名《国魂》《银狐》《成吉思汗的后代》,由弗谢沃罗德·普多夫金导演,奥西普·布里克和诺维申诺夫编剧。1933年4月7日,《申报》为《亚洲风云》进行广告宣传:“苏联影片,切合时事。大刀队示威作,只有大刀长枪,没有媚眼浅笑,只有铁拳铜臂,没有粉臂肉腿。不要妥协,只要拼命,不要屈服,只要奋斗。苏俄影片最负盛名之作!充满了活泼的生命,暗示了前途的光明。指出了奋斗的途径,加强了反抗的决心!”[3]111 该影片主要讲述“十月革命”胜利后,一位蒙古普通牧民贝尔带着珍贵貂皮到英国军队干涉的白俄占据的要塞市场出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皮货商人对之进行强行低价收购。之后,贝尔不堪忍受凌辱与他们发生激烈冲突,独自逃往大漠。后来,贝尔决定加入当地游击队来抗击白俄军队,不幸被捕。在被执行枪决之时,他却被敌人发现其竟然属于成吉思汗的后裔,随之被扶植为蒙古傀儡政权的领导人。但是,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贝尔却毅然走上了反抗异族压迫的道路。后来,他借助成吉思汗子孙的名义率领蒙古境内的诸多游牧民族,以风扫残云之势,驱逐异族统治者并取得最终胜利。《亚洲风云》精心塑造了贝尔这位有思想觉悟的蒙古牧民形象,具有完整的叙事结构和浓厚的人种学色彩,充分展示了被压迫民族不甘屈服,敢于抗击强暴的伟大力量,这可能是鲁迅喜欢本影片的深层原因。1936年10月10日,《鲁迅日记》记载:“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并邀玛理往上海大戏院观《Dubrovsky》,甚佳。”[2]626《Dubrovsky》即《杜波罗夫斯基》,上映之时译作《复仇艳遇》。该影片是A· V·伊万诺夫斯基根据俄国作家普希金小说改编而成,由苏联林飞影片公司出品发行。《复仇艳遇》主要讲述杜波罗夫斯基的土地被当地贵族特耶罗库耶夫强势征收,杜波罗夫斯基为此气愤不已,团结一大批农奴企图劫富济贫,期间他借机潜入特耶罗库耶夫的家中,却疯狂地爱上特耶罗库耶夫的女儿玛莎。后来,他由于放松个人警惕,直接导致悲剧发生。特耶罗库耶夫出于个人利益考虑,将女儿玛莎成功嫁给了当地老贵族。之后,杜波罗夫斯基开始变得心灰意冷,被迫到国外过着隐居生活。鲁迅在观看完影片之后,评价颇高,当晚即写信向黎烈文和黄源二人推荐。后来,许广平深情回忆说:“最后看的一次《复仇艳遇》,是在他逝世的前十天去看的,最令他快意,遇到朋友就介绍,是永不能忘怀的一次,也是他最大慰藉,最深喜爱,最足纪念的临死前的快意了。”[4]203可见,《复仇艳遇》在鲁迅观影经历中具有特殊意义,是鲁迅念兹在兹的苏联电影。
(二)社会建设题材
此种题材电影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高度宣扬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以此彰显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生路》《雪耻》《傀儡》为代表,它们初步奠定苏联早期电影重思想、轻形式,重教育效果、轻娱乐功能的基本倾向。1933年2月19日,《鲁迅日记》记载:“夜同广平往上海大戏院观苏联电影,名曰《生路》。”[2]362 《生路》原名《人生大道》,是苏联第一部有声影片,由尼古拉·厄克任导演。当时,《申报》广告如此宣传:“苏联五年计划成功之代表作!在沪开映第一声!负有伟大的教育使命的大众的影片。没有女人的大腿,没有绅士的高帽,全片充满了生命力,令人感着强烈的刺激!全沪报纸一致赞扬。”[3]109该影片主要讲述苏维埃政府成功改造和教育流浪儿童的故事。“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一群流浪儿童被有关人员在围捕窃贼的时候抓住,后被全部移送到劳动教养所接受思想改造。教养所的指导教师谢尔盖耶夫耐心教育他们。经过耐心疏导,以穆斯塔法·柯尔卡为代表的流浪儿童逐渐戒除不良习气,最后成为优秀苏联公民。《生路》是当时中国翻译的第一部苏联电影作品,在上海各大戏院放映后,迅速引起热烈反响,被许多影评人称为“新艺术的登场”“中国电影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5]。1934年5月31日,《鲁迅日记》记载:“夜同广平往新光戏院观苏联电影《雪耻》。”[2]362《雪耻》是由弗雷德里克·埃尔姆列尔和谢尔盖·尤特凯维奇导演,列奥尼德·卢瓦什夫茨基和弗雷德里克·埃尔姆列尔编剧。该影片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5周年的献礼作品,主要描述钢铁工人挫败反革命技师的蓄意破坏,胜利建成5万千瓦涡轮机的故事。“这儿:有美满快乐的家庭,有奋发有为的群众,有男女相恋的正型,有生产运动的标的!足使顽廉而懦立!涤无能之耻,洗颓靡之习!所以:没有桃色的春梦,没有鲜艳的舞衣,没有大腿和酥胸,没有醇酒与腴臀!剧旨高,题材正!意识伟大严肃!指示人生的正途,辅助社会群众教育!这才是电影!这才是电影的新兴艺术!”[3]167-168鲁迅之所以看重《雪耻》,可能是因为它精心塑造了苏联工人阶级的集体荣誉感,真实呈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建设事业的理想范型。
(三)探险纪录题材
除了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之外,苏联电影广泛借鉴外国电影的成功经验,在摄影技术、艺术手法、思想主题等方面均有显著成绩,许多探险性质的纪实影片被拍摄出来。如《黄金湖》《铁马》《冰天雪地》等,都受到鲁迅特别推崇。苏联幅员辽阔,濒临北冰洋和大西洋,风景奇幻秀丽,是鲁迅心向往之的神秘国度。据许广平说:“他选择片子并不苛刻,是多少带着实地参观的情绪去的,譬如北极爱斯基摩的实生活映演,非洲内地情形的片子等等,是当作看风土记的心情去的,因自己总不见得会到那些地方去。”[4]203 1935年10月3日,根据《鲁迅日记》记载:“夜同广平往巴黎大戏院观《黄金湖》。”[2]555《黄金湖》由弗拉迪米尔·谢内德洛夫导演,伊凡·诺维塞尔采夫、V·托尔斯多夫和米哈伊尔·格罗德斯克共同主演。该影片记述苏联地质学家远征队在阿尔泰地区遭受当地非法淘金盗匪的阻碍,中间森林被恶徒们引燃,他们不得不邀请消防队利用飞机投掷灭火弹,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得以克服重重困难。“纵火焚山八百里红光冲天!飞机抛掷灭火弹科学万能!猛兽毒蛇遍荒野光怪陆离!强徒悍匪霸山林凶恶狠毒!”[3]248《黄金湖》曾经被称为“苏联第一部有声冒险片”,“全片保持了苏联影片一贯的粗线条的沉着精湛的风格”“画面音响都很有特点”[6]。1935年10月4日,鲁迅在给萧军的信中说:“昨天到巴黎大戏院去看了《黄金湖》,很好,你们看了没有?下回是罗曼蒂克的《暴帝情鸳》,恐怕也不坏,我与其看美国式的发财结婚的影片,宁可看《天方夜谭》一流的怪片子。”[7]560 1936年10月4日,《鲁迅日记》记载:“鹿地君及其夫人来,下午邀之往上海大戏院观《冰天雪地》,马理及广平携海婴同去。”[2]625该影片主要讲述苏联青年救援北极居民的惊险故事。“今日开映苏联林飞影片工厂最新伟大探险声片:冰天雪地!加演苏联新闻片,有详细中文字幕。苏联青年为克服北极奋斗!苏联青年与严酷自然斗争!苏联青年援救北极之土人!”[3]311-312鲁迅在给沈雁冰的信中说:“昨看《冰天雪地》,还好。”[8]162 1936年5月7日,《鲁迅日记》记载:“下午同广平携海婴往上海大戏院观《铁马》。”[2]606《铁马》由加列依任导演,由苏联林飞影片公司出品发行。“铁马”即苏俄研制出来的最新最精锐的水陆两栖坦克炮车队。《铁马》“是我国国民所需要的名片!为学生们军事训练的实践!大明星薛木洛夫,美艳女星奥孔诺丝克耶合演,威武滑稽趣情军调巨片”[3]306。此种题材电影不仅能够开阔视野和增长见识,而且可以培养科学精神,是鲁迅体验不同社会人生的重要方式。
二、上海时期鲁迅何以对苏联电影产生执念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鲁迅思想逐渐“向左转”,他开始关注俄苏文学发展状况,并且积极译介卢那察尔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是较早把苏联电影理论译介到中国的代表人物。1932年,中苏全面恢复外交关系,苏联电影随之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受到许多影迷的追捧。早在1927年7月15日,明星电影公司创办的《明星特刊》曾经刊载罗树森的《俄国电影事业最近之调查》一文,他指出:“像乌云受到了一线光明一般,走到了光明的路上,俄国现在的电影事业已是成功了,并且也很发达……俄国电影事业的前途,很有希望而伟大,因为他们电影界,各国的美与成功点都有,而各国电影界所有的缺点,却都没有的。”[9]1930年7月,田汉主编的《南国月刊》第2卷第4期刊出了“苏俄电影专辑”,这是我国最早的苏联电影专刊。田汉在“卷头语”中说,苏联是把电影“这工具使用得最好的国家,所以革命十几年来成绩很有足观,收的效果也很大。他们的电影专门家在这十年以来想写什么干些什么,我们有充分去理解它的必要与价值。他们真比我们进步得多了”[10]。他认为苏联电影不仅有丰富的革命内容,而且“就连技术上也站在电影时代尖端了”,“我们译着德、美、日诸国批评家论他们(苏联)电影艺术的论文时,真是觉得又是欣羡敬佩,又是感愤兴起。何时我们也能做这样的电影工作,放出世界的一些惊异来”[10]。可以看出,苏联电影不仅真实地反映本国国内革命战争和社会建设的图景,而且摄影技术也不断追赶世界潮流,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初步形成了电影制作的“苏联特色”,为中国早期电影发展提供了范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夏衍说:“被欧美的伤感主义和色情主义的影片食伤了的我们,在第一次接触这些苏联影片的时候,谁也会感觉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空气。”[11]93-94因此,上海时期鲁迅青睐苏联电影也在情理之中。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如何有效防止国内封建势力反扑,怎样遏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妄图颠覆苏维埃政权,成为苏联当局直接面临的棘手问题。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和苏联展开激烈竞争,可谓火药味十足。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曾经陷入困顿,许多人希冀借助苏联经验来为中国革命谋取出路。毫无疑问,电影艺术是有效窥探苏联革命图景的重要窗口之一,对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具有较大的诱惑力。“总的来看,苏联电影因其真实的生活题材、创新的艺术手法、典型的人物形象,在世界影坛上取得了较高的影响力。而鲁迅这一时期对苏联电影的关注,可视作其政治立场的体现”[12]。因此,苏联电影的基本特征和鲁迅的左翼立场是契合的,鲁迅对其高度推崇也不难理解。1934年10月11日,《鲁迅日记》记载:“夜同广平往上海大戏院观《傀儡》。”[2]478《傀儡》由雅科夫·普罗塔扎诺夫、波尔菲里·波多比分别任导演和编剧,具有强烈的寓言讽刺特征,被称为“世界政治舞台大写真”。该影片讲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恐惧苏联革命的社会影响力,他们企图操纵苏联周边弱小临国,幻想和他们共同联合进攻苏联,但最后却以失败告终。1935年1月29日,《鲁迅日记》记载:“下午同广平携海婴往上海大戏院观《抵抗》毕,至良如吃面。”[2]513《抵抗》由谢苗·铁木辛哥任编剧和导演,属于黑白有声片。该影片记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两位服务于法国和德国的俄罗斯狙击手在战场上奇迹相遇。“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他们在爱国主义思想感召之下,纷纷回归祖国参加革命,希望为国家贡献自己力量。总体来讲,《傀儡》和《抵抗》都真实地呈现了苏联成功瓦解外国敌对势力干涉和追求民族解放的艰辛历程,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借鉴作用。
毋庸讳言,20世纪30年代,美国好莱坞电影凭借着现代摄影技术和独特艺术魅力风靡世界电影市场,受到许多电影爱好者的无限迷恋。毫无疑问,上海时期鲁迅喜欢观看美国好莱坞电影,尤其青睐剧情片、探险片、喜剧片和科幻片等。但是,鲁迅对中间夹杂的色情因素和文化殖民倾向高度警惕,提醒人们早日认清好莱坞电影工业的深层本质。“侦探片子演厌了,爱情片子烂熟了,战争片子看腻了,滑稽片子无聊了,于是乎有《人猿泰山》,有《兽林怪人》,有《菲州探险》等等,要野兽和野蛮登场。然而在蛮地中,也还一定要穿插一点蛮婆子的蛮曲线。如果我们也还爱看,那就可见无论怎样奚落,也还是有些恋恋不舍的了,‘性’之于市侩,是很要紧的”[13]443。可以看出,鲁迅对待好莱坞电影的立场是矛盾的。一方面,上海时期鲁迅在写作和翻译工作之余,经常出入各大影院观看好莱坞电影,有时对其评价颇高;另一方面,鲁迅在观影之后也对它们进行深刻反思,敏锐地觉察到好莱坞电影具有多副面相,在给人们带来休闲娱乐的同时,部分消极颓废因素也非常明显。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鲁迅对同时期苏联电影总是称赞有加,几乎没有流露出任何不满情绪。1936年4月13日,《鲁迅日记》记载:“晚张因来。萧军、悄吟来。饭后邀三客并同广平往上海大戏院观《Chapayev》。”[2]601《Chapayev》即《夏伯阳》,又名《恰巴耶夫》,是由谢尔盖·瓦西里耶夫导演,根据苏联作家A·富尔曼诺娃和D·富尔曼诺夫同名小说改编,1934年由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出品。据相关资料佐证,鲁迅曾观看过电影《夏伯阳》两次。第一次应该在1935年左右,鲁迅是在苏联大使勃加莫洛夫夫妇带领之下,和茅盾、黎烈文、宋庆龄、史沫特莱等人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共同观看的。当时,《夏伯阳》还尚未在上海各大影院公开放映。该影片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精心剪辑故事场景,主要讲述苏联国内战争时期英雄人物夏伯阳的革命传奇故事。夏伯阳本来出身于农民家庭,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缺乏集体主义思想观念,革命觉悟不高,但他富有军事指挥才能,英勇善战,后来在政委克雷奇科夫的深刻影响下,逐渐戒除旧军队长官的不良习气,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武装头脑,终于成长为具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共产主义战士。“我感受到了这种关注性格、具有深刻现实性、面向人的艺术的亲切和可贵。这部影片一时间成了标准,在许多年中被视为艺术性的最高尺度和极致境界”[14]。该影片的题材内容富有革命色彩,所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性格鲜明,大量运用蒙太奇手法,思想主题鲜明,后来成为中国左翼电影制作的经典样板。
三、鲁迅苏联观中的“洞见”和“不见”
李浩说:“电影被喻为‘装在铁匣子里的大使’,它是被赋予意识形态内核的文化形式,是从业权力掌握者对其他阶层进行权力话语传输的有效渠道,对意识形态的宣传是它的重要功能。”[15]作为一种视觉艺术形式,苏联电影真实地反映了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建设的伟大成就,有效地验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引领作用。鲁迅说:“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16]19鲁迅在《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我们不再受骗了》《祝中俄文字之交》《答国际文学社问》《〈争自由的波浪〉小引》等文章中,高度评价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意义,严厉抨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妄图瓦解苏联的险恶用心,这就涉及鲁迅的苏联观问题。“俄国大改革之后,我就看见些游览者的各种评论。或者说贵人怎样惨苦,简直不像人间;或者说平民究竟抬了头,后来一定有希望。或褒或贬,结论往往正相反。我想,这大概都是对的。贵人自然总要较为苦恼,平民也自然比先前抬了头。游览的人各照自己的倾向,说了一面的话”[17]317。这里,鲁迅对苏联的认识判断看似具有科学依据,但是,部分虚假幻象也是明显的。实际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建设过程中的矛盾问题,并没有在苏联电影里面得到呈现。正如安德烈·巴赞所说:“一切的艺术,即使是最现实主义的艺术也摆脱不开共同的命运。它不可能把完整的现实捕入网内,它必然漏掉现实的某些方面。无疑,技术的进步和运用的得当会使网孔变得细密,然而,仍然需要在各类现实事物中进行一定的选择。”[18]287事实上,电影艺术在如何保留和摒弃社会历史方面,除了要遵循导演意图之外,还受到政治语境、意识形态、领导意志等不同因素制约。因此,“完整电影”几乎就是一个美丽神话。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鲁迅曾经通过瞿秋白、冯雪峰、曹靖华等人,部分获取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建设的基本信息,但是鲁迅毕竟没有亲自踏过苏联土地,许多消息来源实际并不可靠。1931年左右,鲁迅在阅读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记》和林克多《苏联闻见录》之后,也曾经产生到苏联实地考察的念头,但由于当时国内政治环境严峻、身体欠佳等客观原因不得不作罢。近年来,随着苏联历史档案逐渐解密,许多历史内幕得以公开。比如,“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国内贸易国有化政策、余粮收集制等都存在失误,严重激化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现实矛盾。1936年前后,为了全面扫除政治“反对派”的潜在威胁,斯大林开始实施“大清洗运动”和“红色文化统制和禁书运动”,大批党政军领导人、知识分子、革命群众受到残酷迫害,苏联革命出现了历史性倒退,普通民众顿时陷入恐慌,但这并没有在苏联电影中间得到呈现,鲁迅当然也就无缘知晓。对于苏联国内的复杂矛盾,鲁迅可谓是一个隔膜的观者:“‘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智识阶级就要饿死’——一位有名的记者曾经这样警告我。是的,这倒要恐怕使我也有些睡不着了。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19]444。与此相对,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和纪德都曾受邀亲自考察苏联,并分别把个人考察见闻写成《莫斯科日记》和《访苏归来》。特别对于纪德来讲,这次苏联之旅是一种“震惊体验”,他不仅切实看到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但也敏锐地察觉到个人崇拜和极权政治在苏联逐渐蔓延。毫无疑问,纪德的认识判断是合乎现实的,并且早已经得到历史验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孙郁说:“纪德对苏联有赞扬,也有批评,那看法才是知识分子的看法,独立的思想甚多,没有被苏联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囿。而中国知识界判断苏联,是随着苏联官方的导论而体察的。在中国,对苏联的态度一向是两种,要么是好,要么是妖魔化。在汉语言的语境里,分辨思想的明与暗,也确实是一大难事。”[20]26
事实上,鲁迅对苏联的误读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特殊语境中,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加上鲁迅对政治斗争的游戏规则缺乏认知,他可能并不完全清楚革命的复杂多义。苏联在政治革命和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方向偏离,对鲁迅来讲当属陌生化存在,那种远距离关照注定不能穿透历史迷雾。“革命的残酷,清党的无情,生态的破坏,都被鲁迅的笔触省略了。因为远离血色的俄罗斯,他无法体验那里的日常生活的变化。以诗的感觉理解政治与文化,盲点自然会存在其间”[20]269。另外,在“红色的30年代”,“左”倾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肆意蔓延,二元对立成为很多人惯常的思维模式,“中间地带”几乎被严重忽略。可以说,鲁迅后期对“左联”内部矛盾的评价判断,以及对苏联革命的想象认识,多少都带有简单机械的弊病。比如,鲁迅说:“我们的痈,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它们自身正在崩溃下去,无法支持,为挽救自己的末运,便憎恶苏联的向上。”[19]440此时,鲁迅苏联观的“洞见”和“不见”已经得到有效诠释。
参考文献:
[1] 刘素.鲁迅与在沪放映的早期苏联电影[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0(2):75-81.
[2] 鲁迅.鲁迅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李浩,丁佳园.鲁迅与电影:鲁迅观影资料简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
[4] 许广平.回忆鲁迅在上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
[5] 凌鹤.评《生路》[N].申报,1933-02-13(2).
[6] 文波.黄金湖[N].新闻报,1935-10-06(1).
[7] 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 鲁迅.鲁迅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 罗树森.俄国最近电影事业之调查[N].明星特刊,1927-07-15(1).
[10] 田汉.卷头语[J].南国月刊,1930(4):1-4.
[11] 夏衍.夏衍电影文集[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12] 刘素.自然与艺术:鲁迅与写实电影的跨界对话[J].电影文学,2017(16):90-92.
[13] 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4] 贺红英.夏伯阳:一种“苏维埃神话模式”的确立[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47-52.
[15] 李浩.“看”与“被看”:胡蝶·电影·鲁迅[J].上海鲁迅研究,2005(1):245-255.
[16]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7] 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8] 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崔军衍,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
[19]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0] 孙郁.鲁迅与俄国[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7BZW152);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2019GGJS156);河南高校科技创新人才(人文社科类)支持计划(2021-CX-012);信阳师范学院南湖学者青年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禹权恒(1980—),男,河南泌阳人,文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及鲁迅研究。

 [11:30] 韩国女篮U18 VS 马来西亚女篮U18
[11:30] 韩国女篮U18 VS 马来西亚女篮U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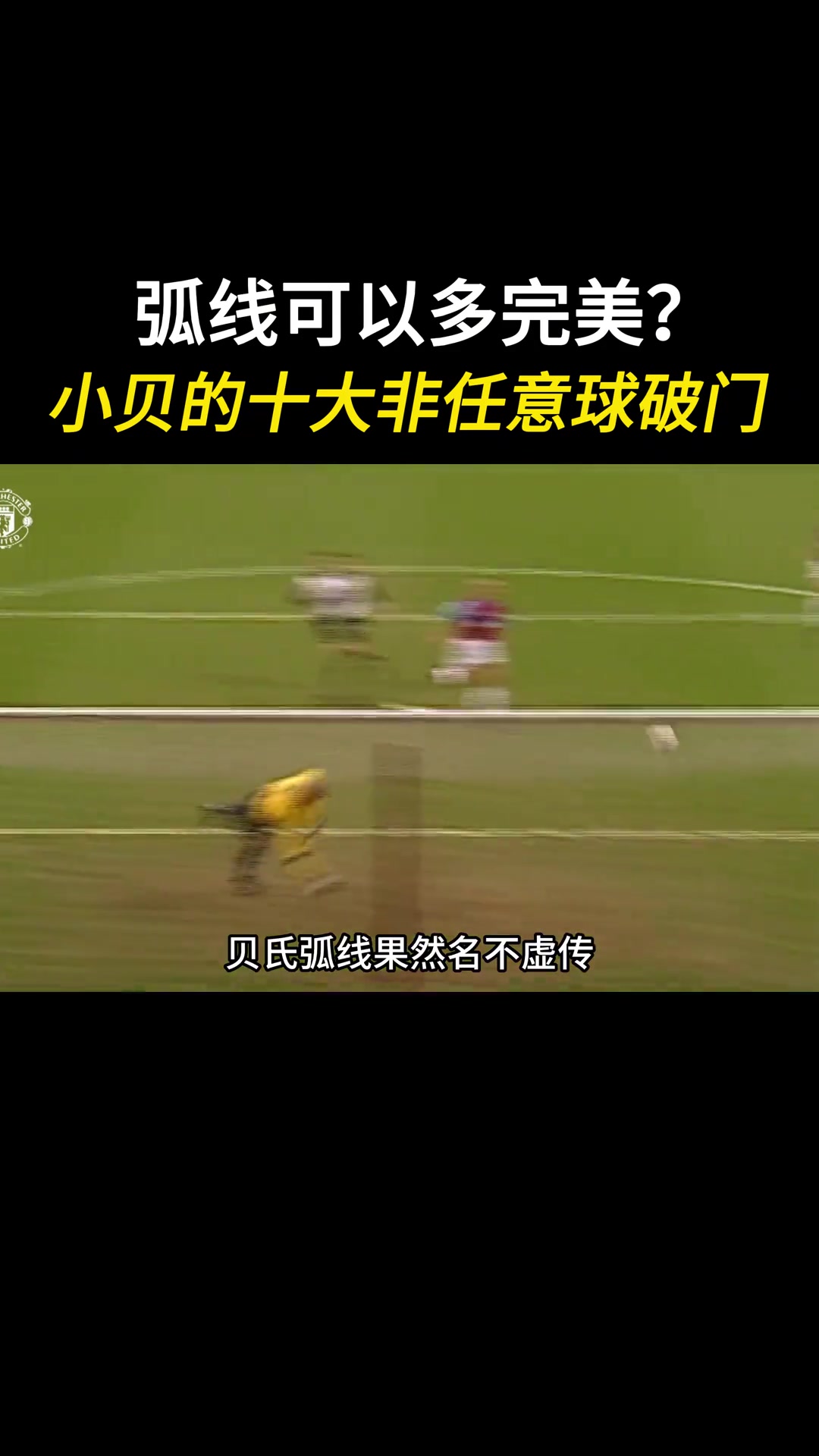






 富安健洋:只要最终成功了受伤也没关系,本赛季直指英超冠军
富安健洋:只要最终成功了受伤也没关系,本赛季直指英超冠军